

油画《送别》 靳尚谊 作 资料图片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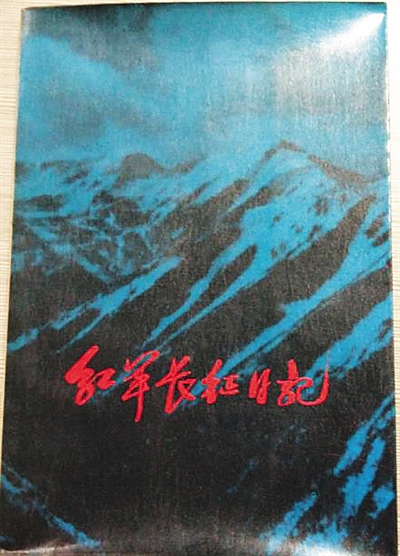
《红军长征日记》。 资料图片
文记者 郑彤
百折不挠历经沧桑岁月,众志成城写就壮丽诗篇。二万五千里风雨历程,二万五千里步履如歌,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,又值重九,那些长征路上的重阳节的故事,也再次激荡出阵阵的历史强音……
每逢重阳,乡情、亲情,便浓如酒、融入墨,绽放成思念的模样。但在毛泽东眼中,思念亲人之际,更应只争朝夕。于是,1929年的重阳节,闽西山区金菊遍野的景色,便添增了诸多豪迈:“人生易老天难老,岁岁重阳,今又重阳,战地黄花分外香。一年一度秋风劲,不似春光,胜似春光,寥廓江天万里霜”。
巧合的是,在毛泽东填下这阙《采桑子·重阳》的6年之后,1935年的重阳节,他正率领红一方面军挺进至六盘山下,并于次日翻越六盘山,吟诵出大气磅礴的《清平乐·长征谣》:“天高云淡,望断南飞雁。不到长城非好汉,屈指行程二万。六盘山上高峰,红旗漫卷西风。今日长缨在手,何时缚住苍龙?”
是啊,有了坚定的信仰,再艰苦卓绝的岁月,也会有光明的守望!翻开一本本泛黄的日记,冲锋号仿佛就在耳畔,长征路上的重阳节的记忆,也透过历史的硝烟,沉淀成一曲曲英雄的赞歌。
1934年的重阳节
“跨过于都河,正当夕阳西下,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,心情很激动,不断回头,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,告别在河边送行的战友和乡亲们。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,不胜留恋。主力红军离开了,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,一定会遭受敌人残酷的镇压和蹂躏,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。依依惜别,使我放慢了脚步,但‘紧跟上!紧跟上!’的低声呼唤,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。”(《红军长征·回忆史料》,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)
1934年10月10日,中央军委发出了战略转移的命令。10月16日,中央红军从瑞金启程。这一天,正是甲戌年重阳。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,在率部从福建征战回瑞金一个月后,再次出发。根据地里,弥漫着依依不舍的亲情。
“十月十六日
由古田至新陂。”(《红军长征日记》,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)
这个重阳,红军电台的奠基人、红军无线电通讯事业创始人伍云甫的日记只有简短的一句话。
“十月十六日
晚饭后开始新的移动,到山王坝宿营。(三十里)”(《红军长征日记》,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)
这个重阳,红一军团保卫局战士童小鹏,也仅用了短短18个字,仓促地写下了他的节日日记。对于这位后来历任国务院副秘书长、中央办公厅副主任、中央统战部副部长、全国政协常委的福建长汀人来说,这个重阳,记忆犹新。他在后来又回忆了诸多细节:
“16日上午,一切准备工作都作完了,把住地群众的家里和门院打扫得干干净净,水缸也挑满了水,有些同志还专门割了一捆草送到牛棚里‘慰劳’黄牛哩!群众则一再感谢红军,妇女们一再检查红军的衣服哪里还有一些破绽,想给他们缝上几针。青少年们则围着‘红军哥哥’一起唱革命歌曲,希望打了胜仗就回来同他们一起开庆祝大会。
为了避免敌机的侦察,到下午5时才出发。部队整齐地前进,群众热烈地欢送,和往常出发打仗时一样,并没有异常的感觉。”(《万里长征亲历记》,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)
红军出发了,有谁能够想到,这次转移,竟然穿越了半个中国;有谁能够想到,这次转移,一走就是二万五千里!
“在部队行进的道路两旁,乡亲们一面跟着队伍往前走,一面将鸡蛋、糯米团往战士的口袋里装,有的拉着我们战士的手问‘什么时候回来?’有的忍不住地‘呜呜’哭了起来。一时间,队伍成了军民汇集在一起的人流……
这时,全师的指战员们心情异常沉重。大家都为红军主力离开根据地后人民的安全担忧,许多人泪洒衣襟,同乡亲们依依惜别,为检查部队的群众纪律,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带着几名干部暂时留在后面,并给乡亲们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,告诉乡亲们:‘我们一定会回来的!’”(《红军长征·回忆史料》,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)
这个重阳节,对于红一军团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来说,既有些遗憾又有些激动。这位在反围剿战役中战功赫赫、荣获“二等红星奖章”,后来成长为共和国上将的湖南伢子,也告别了夹道送别的亲人,和战友们一起,踏上了新的征途,最终走向了全面胜利。
1935年的重阳节
“十月六日
出发到张义铺(七十里)。二十五军占领泾川。”(《红军长征日记》,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)
1935年10月6日,乙亥年重阳。离开中央苏区整整一个农历年了,童小鹏和他的战友们走过了一处又一处的险境、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战斗,抵达陕甘宁交界的六盘山下。前一天在常家集受到的欢迎,令他心中颇暖,“已是回民区域,这些回民的确很好,沿途均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拥挤着来看……入宿营地时,更受到他们亲热的欢迎,帮烧水、购物,这种受群众热情欢迎是出藏人区以来的第一次!据说前二十五军曾经此,纪律很好,故这次我们来时,他们都相信‘红军是保护他们的’。”
与童小鹏的喜悦不一样,同一天,在红一、四方面军于当年6月在懋功会师后,到红四方面军工作的伍云甫,正随着按张国焘命令南下的大军,在四川卓木碉休息。连日来,“天气大多昼晴夜雨,附近粮食困难。”不过,令他和一些战友更加不安的是,就在头一天,张国焘在当地一座喇嘛寺庙里,召开高级干部会议。会议上,张不顾朱德总司令、刘伯承参谋长和徐向前总指挥的反对,以多数通过的名义,形成决议,公然另立中央。
这个重阳,红一军团一师的江西籍战士萧锋也和战友们在宁夏同心县城——半个城,迎来了难得的休息。这位后来历任第三野战军二十八军副军长、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的共和国少将在日记中写到,他们在10月5日抵达此地后,“老乡告诉我们,有一支红军曾到这带活动过,土豪都被打光了。我们看到破窑洞的矮墙壁上确有标语的痕迹:‘打土豪分田地!’‘苏维埃万岁!’‘共产党万岁!’‘红军万岁!’对了,肯定是陕北红军写的标语。我们的落脚点快找到了,毛主席计划的抗日阵地快到了,大家既激动又高兴。”“军团首长决定在此休息一天,进行整顿,收容掉队人员,整好军容风纪进苏区。”(《长征日记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)
“登高而招,而见者远!”从重阳到重阳,战地黄花分外香!1936年10月9日和22日,红四、红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(今属宁夏)与红一方面军会师,中国工农红军持续两年的长征全部胜利结束。胜利结束的次日,恰是丙子重九。
“10月23日 晴
凌晨4时出发,天亮即到兴隆镇,与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会合,一师直属队在街上欢迎我们。下午3时开营以上政治干部会议,5时开联欢大会,一师政治部表演新剧。”(《王恩茂日记》,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)
“十月二十三日 晴
本军在兴隆镇一带休息,与红一师三团联欢,并组织参观团。”(《红军长征日记》,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)
对于刚刚结束长征的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、政治部秘书长王恩茂等指战员来说,这一天,终于可以在邻接甘肃会宁县城不远的宁夏兴隆镇,稍微放松一下了。但更多的红军将士,已厉兵秣马,准备新的战斗。
这个重阳,福建武平籍红军战士林伟在日记中写下:
“十月二十三日 (晴)
今天我们在兴仁堡休息,敌情很紧张,可能需要在此一战,才能继续东进。蒋匪军无视全国抗日运动,仍然要打内战,弄得困难日益严重,十日,日寇川樾大使特见蒋会谈。十八日,川樾又与亲日派的外交部长张群会谈。昨天,蒋介石从南京亲自飞陕,并调蒋鼎文率中央军十多个师入陕,监视张学良、杨虎城行动。(《“战略骑兵”的足迹》,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)
同一天的伍云甫,已和战友们行军八十里,抵达甘肃屈吴山脚下的打拉池:
“十月二十三日 晴
六时出发,至打拉池(约八十里)。一方面军电台十二分队、十五分队驻此地。”(《红军长征日记》,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)
“你用平平仄仄的枪声
写诗
二万五千里是最长的一行
常于马背构思
便具有了战略家的目光
战地黄花如血残阳
成了最美的意象……”
在毛泽东的笔下,“长征是宣言书,长征是宣传队,长征是播种机”;在任先青的《诗人毛泽东》里,长征,则具象成一行壮丽的诗句。但就是这样一行诗句,便于重阳的漫山黄花间,裹着金秋的喜悦,唱响了大气磅礴的红色传奇,嘹亮了东方!
网友回帖
www.hkwb.net AllRights Reserved
海口网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不得复制或转载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:46120210010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: 0898—66822333 举报邮箱:jb66822333@163.com 琼ICP备2023008284号-1 |

7b961540-5a61-43f5-b923-f3870aecc578.jpg)
2e284966-848c-4d83-be24-fcc502f71443.jpg)





